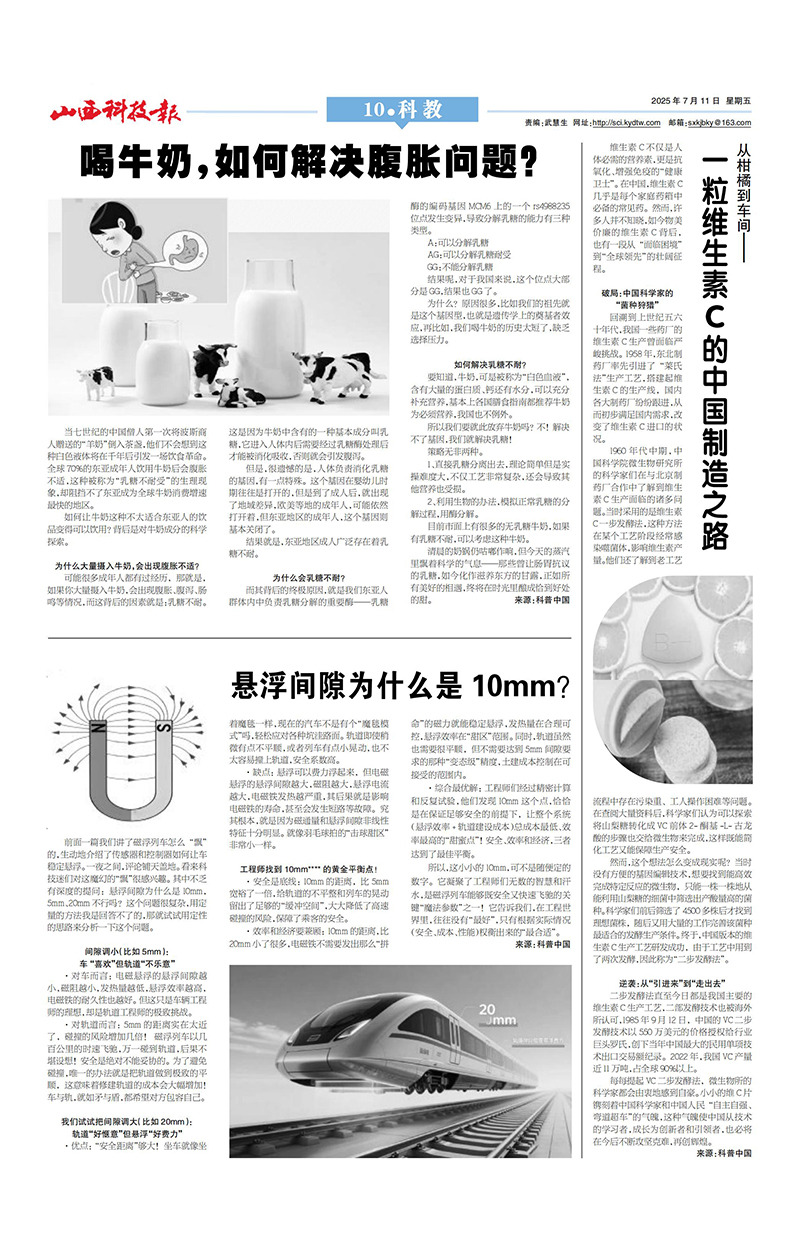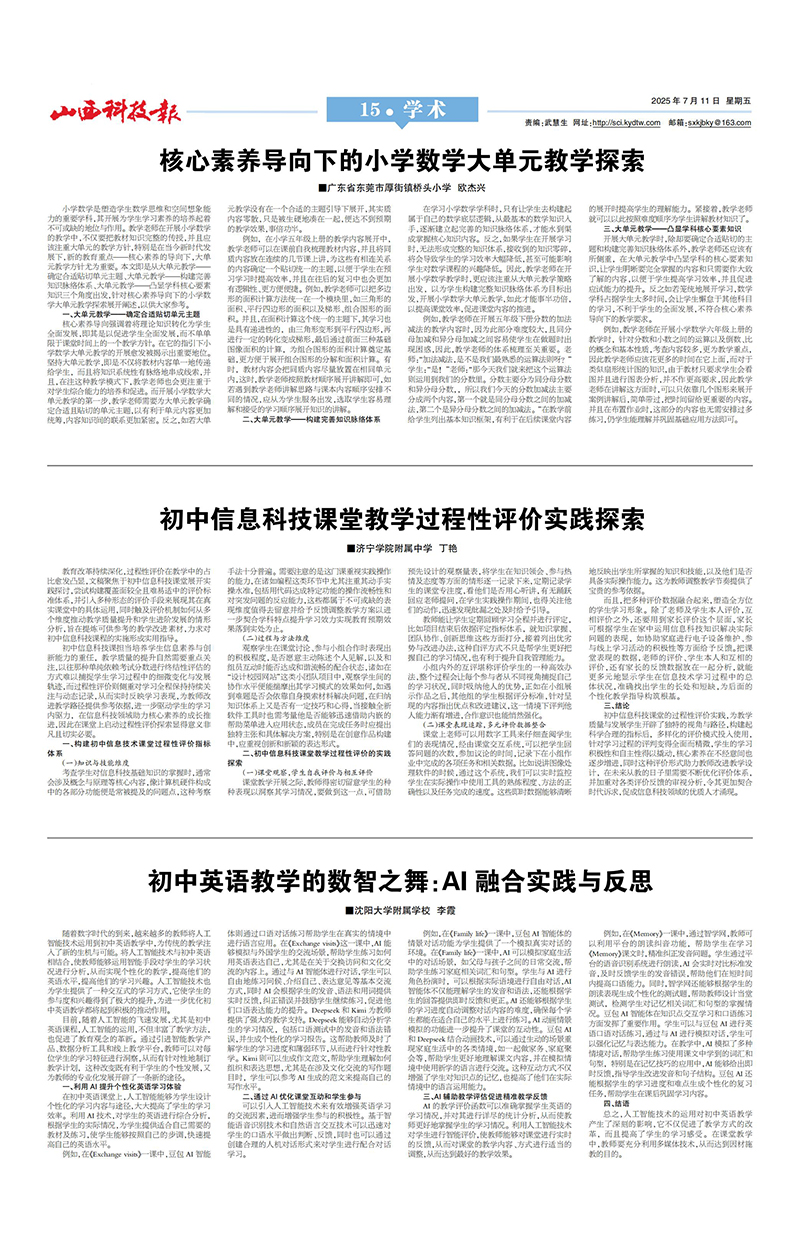04:教育
任诗铭
当那辆颠簸的长途客车终于在县城汽车站停稳时,我提着行李踉跄走出车门,浑身仿佛被车轮碾过一般酸痛难忍。站外已是暮色四合,灰蓝的天空中浮着几颗疏星,微弱的清辉之下,小小的县城被拢在初秋薄暮里,显出几分朦胧的安静。此刻,我忽然想起临行前老师的一番话:“你确定要去这所学校吗?支教可是很辛苦的!”眼前的一幕使我对这个小城无比失望:车站招牌上昏暗闪烁的灯光,零星行人的模糊身影,更别说远处被风沙吹得停不下来的树叶摆动。
一种巨大的失落感无声地攫住了我,我的决定适合自己吗?我一个人能给这里的学生带来多大的改变?我攥紧行李箱的拉杆,冰凉的金属触感直抵心底。暮色渐浓,晚风裹挟着黄土地特有的干燥尘土气息扑面而来,呛得我微微蹙眉。
翌日清晨,我便站在讲台之上。站定之后,我深吸一口气,带着些许紧张,尽力以清晰响亮的声音喊出“上课”。然而回应我的,却是一阵低低的、参差不齐的“老师好”。抬起头,我看见讲台下几十张青春面庞,眼神中混杂着好奇、试探,甚至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漫不经心。我心头微微一颤,努力稳住心神,摊开精心备好的教案,开始讲述第一课。我自以为早已谙熟于心、字字珠玑的讲解,如同抛入深潭的石子,却只激起几圈浅淡涟漪,便迅速被沉寂吞没。学生们眼神渐渐飘忽,甚至有人悄悄埋首书页之间,只留下头顶乌黑的发旋给我看。当粉笔在黑板划出尖利声响时,粉笔灰纷纷扬扬飘落,竟沾满了我的西装袖口。我下意识地拂拭,指尖却只染上一片灰白,那粉末仿佛带着刺,隐隐扎着我的心——这细碎粉末,原是我曾避之唯恐不及的微尘,如今却成了日日相伴的呼吸。初上讲台的豪情,如同被戳破的气球,迅速干瘪下去。
日子在备课、讲课、批改作业的循环中缓缓流过,我心中却日渐堆积起一层厚厚的疲惫与失落。某日课后,一位家长找上门来,脸上挂满疑虑:“老师,您从上海过来,大城市里教法肯定好。可咱们这儿的孩子,就盼着能多学点考试用得上的东西哩。那些花架子,怕耽误了娃们的前程啊。”这话如同重锤,沉沉敲在我心上。我站在窗边,望着窗外那些被秋风染得金黄却纷纷凋落的树叶,心头突然翻涌起深重的惶惑:我满腹的新锐理念,如同精心培育的良种,可为何偏偏落不进新绛这片泥土里,难以生根发芽?我的价值究竟在哪里?那些曾让我热血沸腾的教育理论,在现实的考卷面前,是否真的只是空中楼阁?挫败感像冰冷的藤蔓,悄然缠绕住我的热情。
然而,我未料到转机竟悄然降临。那晚窗外飞雪无声,朔风在古老的窗棂缝隙间低回呜咽。我独自埋首于批改作业的案头,疲惫如同潮水阵阵袭来。就在眼皮沉重欲阖之际,一本摊开的语文作业静静躺在灯下,纸页间字迹娟秀,带着少女特有的清丽:“老师,您知道吗?每次课堂上您对课文的讲解,都让我觉得非常新颖,好像能从课文里看到一个崭新的世界。有时候您虽然也会恨铁不成钢,但我知道这是您在担忧我们的前途。”我的心猛地一热,一股暖流猝不及防地冲撞着心防,原来语文的意义就在于此!这行朴素的文字,仿佛在严寒的夜晚悄然拨动心弦,让我第一次真切体味到这份平凡工作中蕴藏的、足以抵御寒流的温暖。
随着时光推移,我开始尝试将所学理论的有趣之处与课文相结合,真正贴近孩子们的生活。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我带他们进入李白的内心世界,也许他们不能真切地体会浪漫的风格,但我想一定有种子埋入心间。在《插秧歌》中,我不再仅仅聚焦于劳动的崇高,而是询问他们是否熟悉窗外黄土无言的情味,是否见过祖辈在烈日下躬身劳作的背影?我看到许多双眼睛亮了起来。课后,我常常留在教室,不再只是埋头批改作业,而是倾听他们诉说那些只属于少年时代的烦恼与梦想——为解不开的数学题蹙眉,为球场上一次失误懊恼,为悄悄萌动的心事脸红,为遥不可及却又闪闪发光的大学梦而暗暗攥紧拳头。我成了他们倾诉秘密的树洞,分享喜悦的朋友。渐渐地,课上课下,孩子们原本疏离的目光开始融化,如同春阳下的薄冰,话语也逐渐多了起来,有时甚至在我还未宣布下课,便主动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分享他们眼中的世界,讲述村里的趣事,或者急切地询问某个知识点。那份小心翼翼的试探,终于化作了信任的暖流。
一个周末的午后,我偶然漫步于校园深处。绕过几排规整的教学楼,一片古朴肃穆的建筑群豁然眼前。青砖灰瓦,飞檐斗拱,在冬日疏朗的阳光下沉淀着岁月的包浆。廊柱上深深刻着的“民国八年建”字迹,虽经风雨侵蚀,依旧清晰可辨。几株虬枝盘曲的老槐树,枝干黝黑如铁,沉默地守护着庭院。树下,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校工正小心翼翼地擦拭着一口悬挂在亭中的古铜钟。他告诉我,这钟声,自建校伊始,已在此回荡了百年有余,晨昏定省,寒暑不辍。那一刻,指尖抚过冰凉而布满历史印痕的钟壁,一种难以言喻的厚重感与归属感悄然漫过心头。我忽然明白,我所立足的这片土地,并非贫瘠,而是积淀深厚。那些看似朴拙的孩子,他们的血脉里,或许早已浸染了这所百年学府沉静而坚韧的基因。
季节流转,转眼已到了练习的时间。某天清晨,我特意早早来到教室,学生们尚未到校,室内一派宁静,只有金色的晨曦透过高大的老式玻璃窗,斜斜地铺洒在磨得光滑的水磨石地面上。我习惯性地拂拭讲台,指尖却忽然触到一道细小的缝隙。俯身细看,竟是一株纤弱却倔强的嫩绿草芽,不知何时,以怎样不可思议的韧劲,悄然顶开了坚硬的水泥接缝,顽强地探出头来,在清冽的晨光中微微颤动,舒展着两片娇嫩得近乎透明的叶片。叶尖还凝结着一颗细小的露珠,宛如新生婴儿纯净的泪滴。我心头蓦然一震,屏住呼吸,久久凝视着这渺小却无比强大的生命——它无声而磅礴地诉说着扎根的力量:纵然土壤瘠薄,空间逼仄,际遇艰难,只要生命意志不灭,心向光明,总能找到缝隙,向着光亮奋力生长,绽放属于自己的那一抹新绿!这株水泥缝中的小草,不就是无数在平凡甚至困顿环境中努力向上的生命的缩影吗?不正是这所百年老校“自强不息”精神最生动、最细微的注脚吗?
站在讲台上,我凝望着窗外的阳光无声流淌进来,悄然铺满了斑驳的讲台边缘。无数微尘在斜射的光柱里清晰可见,它们无声地浮游、旋转、升腾、沉降,宛如宇宙微缩的星尘之舞,充满了一种静谧而永恒的诗意。回想初到时,自己拂去袖口粉笔灰时那微微的抵触与嫌恶,到如今凝视这光中浮尘的宁静与近乎虔诚的观照,心中已然豁然澄澈:那粉笔灰,原来就是飘散在阳光中的微尘,是教育者每日必须呼吸的空气,更是百年光阴里无数师者智慧与心血的细微结晶。它们终将沉淀,如同无数前辈播撒的种子,化为滋养一代代年轻心灵的沃土。
我缓步走向那面镌刻着杰出校友名字的纪念墙。指尖划过一个个或熟悉或陌生的姓名,感受着那冰凉的铜质或石质的质感,仿佛触摸到了这所学校奔腾不息的脉搏。从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到百废待兴的建设时期,再到日新月异的改革年代,一代代学子从这里出发,走向广阔天地,成为栋梁之材。他们的名字,如同星辰,照亮了后来者的征途。这所朴素的校园,这斑驳的墙壁,这沉默的铜钟,还有那飘飞的粉笔灰,共同构成了一种无声而强大的精神磁场,一种名为“传承”的庄严仪式。
当晨曦初露,清越的钟声再次穿透薄雾,回荡在古槐掩映的校园上空,那声音浑厚、悠远,带着穿透岁月的力量。我再次立于讲台之上,目光掠过台下一张张青春洋溢、如初春花朵般摇曳的脸庞,心中豁然澄澈,充盈着前所未有的坚定与温热:三尺讲台虽微,却托举着无数个鲜活的未来,连接着厚重的过去与无限的远方。也许在这里支教时间不长,但我明白教育种下的并非具体的花籽,而是倾尽全力,为他们营造一个让花能够无所畏惧、尽情开放的整个春天——那微尘浮动的光柱里,那悠远回荡的钟声里,早已映照出、蕴含着无数个喷薄欲出的黎明。